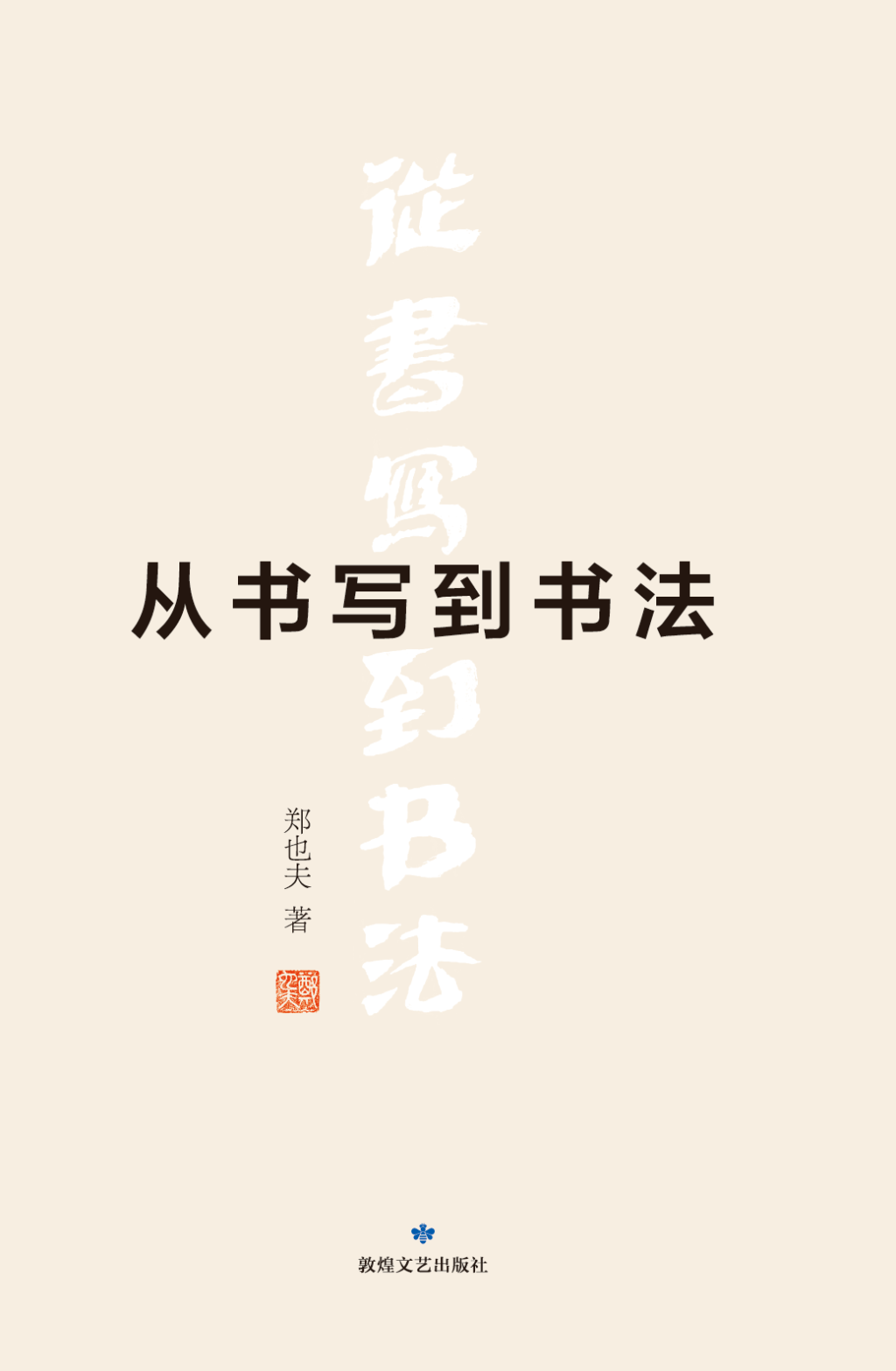
《从书写到书法》,郑也夫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一切看似自古皆然的文化形态,终须经受研究者们的疑问。经典、书籍、书法,莫不如此。大众印象中,历史学家完全依赖于“历史上的”文本记述方得以进行工作、维持这个行当,然而他们早已从文本出发,看见承载文本的物质,将之视为一种媒介。于溯写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倪健写唐代诗歌的“物质过程”,都全不在作品内容或“知人论世”的旧话题上多做停留,而是力求展现曾被遮蔽无视的书写、抄本、传抄、读诵、记忆、形式变异等等环节。
这样的研究,或许可以称作一种在文学史与文献学史之内的“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转向”。那么,当社会学家郑也夫把眼光投向“书法史”时,则把这原本充满着传奇甚至神话色彩(魏晋以来,的确如此)的“家系”拉回到地平线上。“书法的历史”是否如一众“书法史”教材所说,文字从甲骨文肇始,至金文臻于大观,小篆一统,隶书后出,楷、行、草一路走来,书法史即书体的历史、书法家的历史,除在若干细节问题上辨别真伪之外再无疑义?这自然也需要重新被审视、检验,乃至于天翻地覆,要另寻一种范式来讲。
《从书写到书法》正是这样一本书。文字起源的顺序、书体演变的因果、名家的真伪、乃至“书法”这一概念本身的出现时点,不妨重新思考。观看“书法”的方式,亦可从单一的线性转为采用结构的眼光。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被称为“书法”的文化现象?是什么让某些人、某些书写行为被提升为艺术,而另一些则被遗忘?书写从来不是孤立的审美活动,它与行政文书、官私学校、科举考试、雕版印刷均有关联。社会分工与权力结构中某一部分竟然成功得以自我神圣化,并延续至今,这才是令人惊异的问题。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除去社会学家的分析视角,还需一种“历史的想象力”。郑也夫屡屡强调自己讨论历史问题时的两种方法:一是疑古,二是想象。疑古的价值自不用多说,不疑,则无法打破种种早早深入人心的传奇神话。毕竟人心善于在接受之后自动补全,将散落的传闻与论断化作牢不透风的谱系。不像堂吉诃德一样冲撞一番,绝难叫它现出原形。而想象的价值,则在面对史料匮乏的远古与中古书写史时格外凸显:想象是“逻辑的可能性”,是在有限史实与严密推理的双重约束之下,去设想那些史书未载却在逻辑上可能成立的情形。不是以虚构取代事实,而是以思维的连续性弥补史料的中断,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本应存在却未被记录的环节。
因而,在《从书写到书法》一书中,屡屡可见以往未曾讨论通透的新着眼点。以下略举数点。
其一,是对“何为中国书写史之源”的重新追问。哪怕王国维在百余年前便指出金文、甲骨、简牍三者先后不可确指,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通行的叙述仍然从甲骨文起笔,把它视作“中国最早的文字”。而本书欲以证据、逻辑与想象重新回答这一问题,便要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去围猎未知的可能。
先是考古证据:已知的考古发现中,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略早于甲骨文。只因青铜器上的金文铭刻往往字数稀少,因而在起源问题的讨论中被轻视。次则是训诂学问:甲骨文中有“册”字,有学者解释为“玉册”,而郑也夫推测“册”解作简牍更为合理,不仅是简牍,还应当是联缀的简牍,而在联缀出现之前,必定有漫长的单篇简牍的例子。但释字的路径有所极限,还要兼用其他视角。因而作者另辟蹊径,以“字从上到下、行从右往左”的书写顺序,反推出存在一种影响中国书写传统的关键因素,即是特异的书写载体——简牍。
郑也夫把这称作简牍对中国书写顺序的“锁定”,并由此延伸出宏观推论:“初级锁定如上所述,是一小撮文字阶层追求不同文字载体的一致性。二级锁定是秦始皇的书同文。三级锁定是科举制,科考中连字形都必须是馆阁体,书写顺序岂能自选。”
其二,是对“书法起于东汉”的论述。此处的写法,并未采用罗列“书家”“书体”的旧规,而是直接针对书法史常见的“寻根”倾向,从今日可见的痕迹一一回证:甲骨文、金文、小篆,都不应当以“书法”的观念看待。始皇巡行天下,留下多处刻石,旧说出于丞相李斯之手,但这种意见最早出于卫恒(西晋人),离秦始皇时代更近的汉人却未见提及。秦阳陵虎符由小篆写成,王国维说“此符乃秦重器,必用相斯所书”,而作者未知其中证据,不敢轻信。
讨论书法之始,需先有书法的大致定义。作者拟出四条:书写是否以审美为自觉目的,而非仅仅为传意服务;不仅要“写得好”,还要在可被观看、比较与学习的社会情境中,作为审美对象被评价与承认;还需脱离“匿名之迹”,以“某人之书”之名而留存;须看整篇所能达到的高度,不可仅凭抽拈若干精彩字形来断定。因此马王堆的帛书笔势极具生机、活泼流动,却还不能算作书法,一直要等到东汉的蔡邕以“八分书”得名。
这两处是本书对旧题目做新文章的例子。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在寻常知识中发现新题目——从唐太宗时代为他搨写王羲之墨卷的供奉搨书人冯承素连接到敦煌的写经卷子、清以前长期被忽视的魏碑、技艺惊人却无迹可循的僧安道壹,都指向一个疑惑——在书法与书法家出现之后,何以又有那么多被忘记的书法家与精品?无论是正史,或是书法著述,对书法家又做了二元划分:有名者与无名氏。前者多依赖于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与记忆传递,后者被遗忘,但又不算是真正被埋没。其中趣味,又可与后面章节中“馆阁体”与当代书法家的讨论相关联。
通看本书中的各处着眼点,“疑古”与“想象”的风格发挥淋漓尽致。疑古,让掩藏在单线论说之下的书法史从一种“传承有序”的故事变为处处可思考的问题渊薮。想象,让碎断在不同载体之中的书写能够在社会学家的眼光中被置于同一个大结构中映照。
自然,本书既无意于做中国古代书写与书法的百科全书,也无可能覆盖这一题目下全部可讨论的线索。例如在把中古时代的书法家做二元划分时,作者把“有名者”与“士大夫”相连接,视为贵族文化与文治的象征。这种处理,便未遑留意一种特殊情形:当留名的士大夫感受到自己与无名的书写匠人并无差别时,又当如何理解?有这么两个故事,可以讲一讲。
其一,魏明帝时代的重臣韦诞因为擅长楷书,所以宫观的题榜往往是要他来做。有一次工人误把空白的匾额给钉到了殿额,明帝便让少说也年近五十的韦诞用辘轳高高吊起,悬空二十五丈,持大笔去补写。待他被放下来,便在“家令”中明明白白警诫子孙:“绝此楷法”,谁也不许再学!
其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与名相谢安关系密切。谢安请献之写太极殿的榜题,派人送来空白板子。献之此时还做着谢安的长史,却直接叫人丢出去。谢安不满——过去韦诞身为大臣,比子敬你地位更高,不也写了么?王献之丝毫不留情面,回答道:就是因为有这种事,魏国之祚才如此之短。
上述故事,颜之推已做过总结:“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韦诞)遗戒,深有以也。”他又说,“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总之,士大夫书法家不一定能保证自己不与“匿名之迹”背后的平民书法家相隔离。一旦遭遇这种事件,即是耻辱。
这两条故事,实则正说明书法的历史无法用一种单薄的“英雄谱系”描述清楚。它不仅需要结构,还需要更多视角、更多方法以实现多面相、多层级的结构分析。这正是本书的开创价值所在。
那么,再用“书法史”的名目来指代本书,是否足够?有一组词汇堪作思量: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开始,再到各种专门史,“内史”(internal history)与“外史”(external history)的区分已屡见不鲜。用江晓原的话说,内史可理解为对某一学科自身展开的梳理,重心落在学科内部的事件、成就、仪器与方法、典型著作与关键人物,以及由此牵连出的年代学问题;外史则把目光移向学科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考察这一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性质。
“内史”与“外史”的写法,哪种更适宜于中国书法?对单个作者与读者而言,自然是见仁见智。本书以社会结构、文书体制与书写劳动等元素为切入点,实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写法:外部的文化传统、技术状况与制度力量塑造了书写的样式,而这些样式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如何定义“艺术”“文化”和“身份”。当这一点被点明之后,我们对书法历史书写的疑问就自然变作另一种样子:在书法这样的艺术领域,是否仍可能存在“纯粹的内史”?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暂且如此称呼),其媒介性、实用性与象征性始终交织在一起。作者判定“书法起于东汉”,正是因为那时出现了“外部社会条件”——署名、比较、公开展示与评审,书写第一次被社会性地确认为可以被观看、可评论的行为。或许,从此开始,书法的“内史”便不再可能独立存在,而只能在与“外史”的互动中演化。而传统的“书家”与“名作”的书法历史,只是身处于外部社会文化的汪洋之中而不自言的结果。今日读者面对这些记述,原本就应负起补全这些隐含词句的责任。
并不只是书法。二十世纪以来,艺术史、科学史乃至文学史都在发生类似的转向——从对作者与作品的线性叙述,转向关注制度、媒介、受众与权力的关系。本书虽然强调“历史的想象力”,实际上一直在回应着这一潮流。它的主题比起“书法如何发展”,更像是“社会如何使书法成为可能”。
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去谈“书法之美”?在我看来,让书写之人由“众神”回归至世人的行列之中,让修辞赋予的名号不遮挡书写者确有的美学意识,也不掩盖那些尚未自觉的美(如作者在书中谈论到的马王堆帛书),审美才有可能回到人的经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