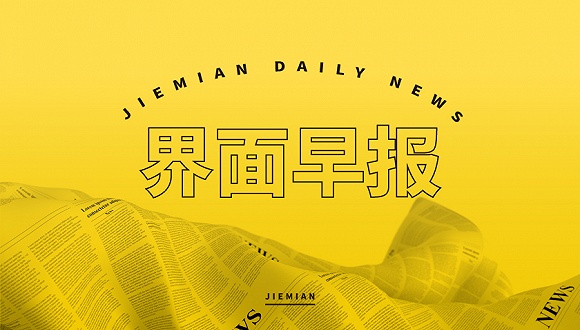《伏尔泰与启蒙之战》,石芳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出版,538页,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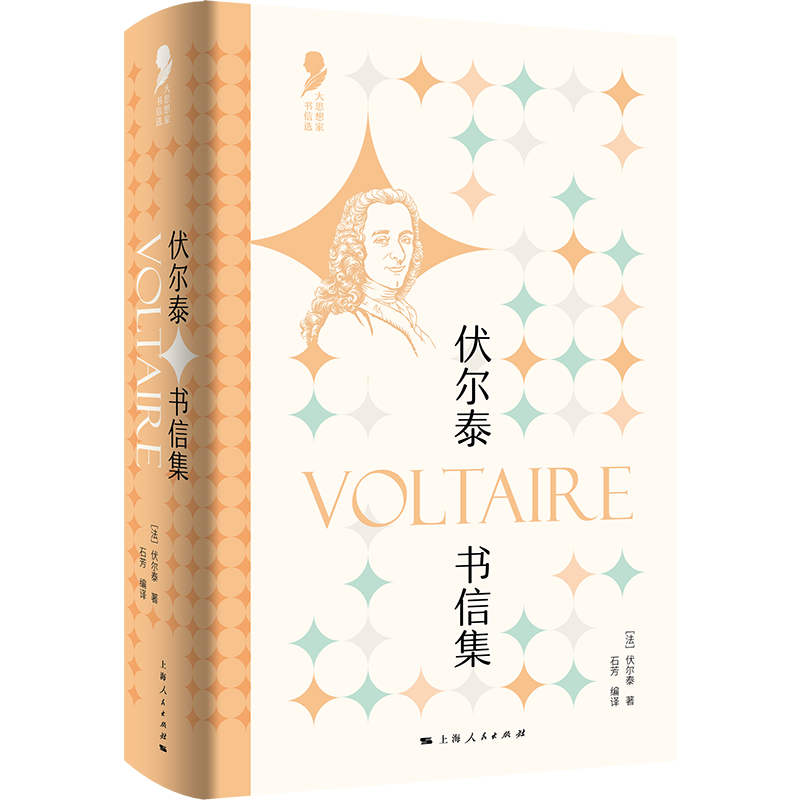
《伏尔泰书信集》,[法]伏尔泰著,石芳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128.00元
自诞生以来,启蒙运动便被视作一个完整的时代现象,既被推崇,也遭诘难。两百多年过去,相关研究浩如烟海,争论绵延不绝。启蒙的意义非常明确,却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其形象也愈加模糊。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固然令人神往——那些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其语言之犀利、洞见之深刻,令人折服,但终究难以解释历史的肌理。启蒙思想何以生成?对时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回响?这些问题无法在观念的推演中得到解答。思想纵有锋芒,若无社会运作的加持,徒劳无益罢。
如再考虑启蒙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将更加棘手。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已然熄火,至革命爆发,尚有近二十年的平静期。其间,第一代和第二代哲人或退隐,或辞世;文人论战几近停息;存世的启蒙哲人大多功成名就,在各类文化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不再像以往那样活跃。社会资源趋紧,阶层流动空间日益受限。许多年轻文人涌入巴黎,试图效仿伏尔泰和卢梭,却多半时运不济,沦为伏尔泰口中的“可怜虫”,或罗伯特·达恩顿所言的“格拉布街文人”,以撰写谤文和色情小说为生,被人讥作“街沟卢梭”(Rousseau du ruisseau)在时代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个时代,可谓启蒙运动已然退潮,而革命风暴尚未到来。于是,越来越少人选择直接将启蒙运动与大革命联系起来,反而视革命的爆发为偶然。如此一来,启蒙运动的位置何在?
然而,正是在摆脱革命叙事的束缚后,观察、解释启蒙运动迎来了新的可能:启蒙本身就是一场独立的社会运动,它无关革命,无关宏大的叙事和高尚的意义。在这样一个文学时代,俯眼尽是社会交际、人际纠纷和权力运作。故此,有必要重视启蒙运动的社会史,关注启蒙时代的文学政治。
当然,这一呼吁并不新鲜。从法国的史家达尼埃尔·莫尔内、丹尼尔·罗什,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英国剑桥学派,再到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皆投身于此。近期,石芳的新作《伏尔泰与启蒙之战,1750—1770》(商务印书馆,2025年)及其编译的《伏尔泰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类似的尝试,填补了国内启蒙社会史的空白。借此契机,我们或可重新回到伏尔泰,一同深入伏尔泰的文学政治活动,以重审启蒙运动。伏尔泰是启蒙社会实践的典型,是诸多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在伏尔泰这里,启蒙展现为一场有一定组织、策略和目的的社会运动。
为卡拉斯一家伸张正义
在“启蒙三杰”里,如石芳所说,相比于思想深刻的狄德罗和卢梭,伏尔泰并无多少思想创见(486页)。当然,伏尔泰善于社会运作,本不以新锐思想见长。最能体现这点的,当属伏尔泰为卡拉斯一家翻案所作的努力。
1762年3月20日,在位于法瑞边境、紧邻日内瓦的费尔奈府邸里,伏尔泰接见了顺道拜访的马赛商人多米尼克·奥迪贝尔,后者向他仔细述说了近期发生在法国南部图卢兹的一桩冤案——卡拉斯案:1761年10月13日,图卢兹费拉提耶街的卡拉斯家,长子马克·安托万自缢身亡;因被怀疑谋杀意欲转信天主教的长子,作为新教徒的卡拉斯一家先被图卢兹市政官大卫·德·博德里格、后被图卢兹高等法院判处有罪,父亲让·卡拉斯遭车轮酷刑而死,余众则被处以监禁和流放;一时间,图卢兹城反新教氛围愈加紧张,新教徒人心惶惶。
听闻此事后,对宗教迫害并不陌生的伏尔泰也震惊于此案之残酷,有意对卡拉斯一家伸出援手。很快,他就行动了起来。3月25日,经过认真思考后,他致信曾任外交大臣的贝尔尼枢机主教,描述了此事在他内心引起的愤怒和忧伤。29日,在给达朗贝尔的信里,他表达了对宗教狂热的不快(《书信集》,270-271页)。不过,伏尔泰依旧不待见新教徒,他对新教徒的无知和狂热仍心有余悸。不久,伏尔泰在府邸约见了在日内瓦避难的皮埃尔·卡拉斯和多纳·卡拉斯两兄弟,因印象不错,才打消了疑虑。4月伊始,伏尔泰开始进行社会运作,他联络各方权贵,如舒瓦瑟尔公爵、负责监管改革宗的国务秘书圣-弗洛朗坦公爵、蓬巴杜夫人等,希望能引起他们关注卡拉斯一案。同时,伏尔泰竭力争取巴黎上层精英的支持,着意让卡拉斯夫人北上巴黎,后者在巴黎获得了不少显贵和新教富人的同情与帮助,并与达朗贝尔、卢森堡夫人、达让达尔夫妇等启蒙要人建立了联系。
1762年6月至7月,伏尔泰伪装成当事人的口吻,以致法国司法大臣的名义,匿名撰写了四本小册子,以争取舆论。首先是《寡妇卡拉斯的信》,讲述了卡拉斯夫人经历其长子死亡的过程;第二本是《多纳·卡拉斯关于其父、其母、其兄的回忆录》,详述了卡拉斯一家的状况;第三本是《皮埃尔·拉卡斯的宣言》,试图证明了其兄之死并无谋杀之迹象;第四本《有关卡拉斯之死和图卢兹审判的原始文件》,包含了《寡妇卡拉斯的信》,并增添了多纳·卡拉斯写给其母的一封信,其中多纳呼吁卡拉斯夫人寻求国王的帮助,以平反此案。四本小册子,在事件描述上可谓动情声色、感人至深,读者莫不潸然泪下。1763年,伏尔泰还就此案出版了正式著作《论宽容》,尽管这部作品的影响力在翌年出版的《哲学辞典》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除了自己的文笔,伏尔泰还非常重视律师辩护状的影响力,他寻求三位著名律师皮埃尔·马里埃特、埃利·德·博蒙和卢瓦梭·德·莫雷昂的帮助。三人共出版了近十篇辩护状,进一步宣传了卡拉斯一案,其效果不逊色于伏尔泰自己的作品。
然而,运作的结果来得很慢。1764年6月4日,御前会议推翻图卢兹高等法院的判决。1765年2月25日,最初主导审判、故意施害的图卢兹市政官大卫·德·博德里格被撤职,他大受打击,精神因而受损。1765年3月9日,历时三年多后,最终复审结果出台,御前会议宣布卡拉斯一家无罪,并决定对他们进行补偿。3月15日后,伏尔泰才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喜极而泣:“我们倾泻出感动的泪水”,“我流着快乐的泪水拥抱多纳·卡拉斯”(166页)。
不过,御前会议这一判决效果非常有限。图卢兹高等法院素以反叛著称,曾坚决抵抗国王征收附加税。在卡拉斯一案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不愿服从撤销判决,王室政府也无意强迫推行,以避免激化矛盾。故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图卢兹地方对新教和卡拉斯一家的敌意不减,卡拉斯一家后来定居巴黎。
这是伏尔泰介入社会事务最为显著的一场活动。当然,这一案件不是在伏尔泰介入后才成为公共事件的。在案件上诉至图卢兹高等法院时,按照规定,卡拉斯一家有权获得一名律师的辩护,此即当时颇为有名的法学家迪奥多尔·苏德尔。苏德尔可谓不畏艰难,不遗余力地为卡拉斯一家辩护,极力证明这不可能是一场他杀案件。但更为重要的是,苏德尔出版了三份文本,力图扩大此案的影响:《为让·卡拉斯先生辩护的陈情书》、《卡拉斯令郎令女的后续》、《关于卡拉斯令郎令女的反思》。为了反驳有关新教徒谋害转信天主教的子女这一谣传,日内瓦的牧师团旋即发表了《庄重声明》,并得到了日内瓦市政理事会的支持。卡拉斯案开始溢出图卢兹城,传播至全法、乃至法国以外的地区。1762年,牧师保尔·拉博出版了《混乱的诽谤》一文,驳斥由此案引发的对新教的诽谤,呼吁宽容和良心自由,并抨击图卢兹高等法院。此作引发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激烈反应,但王室政府有意平息宗教争端,故此事并无后续。
不过,风波并未局限于案件本身。伏尔泰匿名发表的辩护作,瞒不过公众的慧眼,人们很快便发现背后的作者正是伏尔泰。1765年,就在让·卡拉斯平反昭雪后,伏尔泰的死敌弗雷隆就在《文学年代》上质疑伏尔泰对该案证据的判断:既然博德里格对卡拉斯一家的审判出自不可靠的“宗教罪行检举书”(monitoire),是一种“因信定罪”,缺乏实质证据,那伏尔泰的努力不也是一种“因信翻案”吗?(167-168页)。弗雷隆进而指责伏尔泰为卡拉斯平反是出于虚荣,但在倾向于卡拉斯一家和伏尔泰的公共舆论面前,弗雷隆此举显然是在以卵击石。很快,弗雷隆就引起了公愤,耻辱退场(170-171页)。
总之,从中可见,虽然伏尔泰对翻案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他因而也有“欧洲的良心”之美称,但应当看到,伏尔泰的活动是内嵌在旧制度法国社会事件之中的。这些活动和交锋即是石芳新作关注的重点,正是这种以论战为主的文学政治,构成了社会层面的启蒙运动。石芳的新著之所以说是一个契机,正在于让我们看到了这点。

《不幸的卡拉斯一家》,卡蒙特勒(Louis Carrogis Carmontelle)作,1765年,卢浮宫藏。图中描绘了1765年2月案件重审时,卡拉斯一家因受控而被暂时拘禁于巴黎的贡西尔日里监狱(Conciergerie),皮埃尔·卡拉斯及友人奥贝尔·拉维斯向其家人宣读律师埃利·德·博蒙写的辩护状。
论战中的启蒙运动
如其清晰的结构所示,《伏尔泰与启蒙之战》围绕着伏尔泰的文学政治活动,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有关启蒙形象的论战;其二,文人争取权贵的努力;其三,提携后进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时代措置,石芳选择了“反哲学运动”和“反哲人”的概念框架,而非常见的“反启蒙运动”。石芳此举可圈可点,就像她在绪论中论证的那样,原因有二:首先,“反哲学”更加符合十八世纪法国的时代语境:启蒙哲人通常提到的是哲学及其统治,反对者常说的是 “所谓的哲学”,启蒙和反启蒙并非十八世纪哲人和反哲人所熟知乃至使用的概念语词。石芳对此解释道:
“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等启蒙思想家并不知道‘启蒙运动’,他们自称‘哲人’,热情洋溢地谈论‘哲学’、‘哲学精神’,相信‘哲学’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伏尔泰的启蒙经典《哲学辞典》正是按这个意义命名的。相应地,那些反对哲人及其观念的人,往往自称为‘反哲人’,用‘反哲学的’来形容、命名自己的观念和作品。”(11页)
再者,比起“反启蒙运动”,“反哲学运动”牵涉的范围更广,不局限于反启蒙思想,“还包括压制、阻碍哲人及其思想传播的各种权力、机制和活动”(13页)。简言之,它是思想的社会史研究。此研究框架批评的正是以赛亚·柏林代表的启蒙观念史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法国传统的史学中也有存在,近年来的启蒙和反启蒙研究中也不乏此种范式的身影。无疑,这种研究范式与近现代以来的左右派争论紧密相关,如研究反启蒙传统的以色列史家泽夫·斯汤奈尔就是一名左派知识分子(《反启蒙:从18世纪到冷战》,2009年,中译本2021年)。
石芳的这样一种史学考虑,正呼应了开篇所描述的问题背景,而《伏尔泰与启蒙之战》不啻为对观念史研究的一种反正,这在国内学界可谓别开生面。为此,石芳选择了启蒙盛期(1750-1770年)由伏尔泰主导的论战作为切入点。
谈及启蒙论战,伏尔泰必首当其冲。卢梭性格孤僻,1766年后也厌倦了文人争论,决心封笔,不再踏足文坛;狄德罗在论战上“战绩”不佳,且屡次被投入监狱,虽未退出启蒙事业,也未再敢抛头露面;达朗贝尔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身居高位,很少参与论战。格里姆、莫雷莱等启蒙文人在文坛上虽颇为活跃,但影响力有限。能够担任论战领袖,且有能力保障自身政治安全的,只有伏尔泰。
在政治意义上,伏尔泰真正投入到与反哲人和宗教保守派的论战,是在1757-1759年期间。在此时期,发生了“卡库雅克人”事件,与以往的诽谤不同,在此事中,哲人作为一个群体遭到了诋毁,背后则有蓬巴杜夫人的支持。在石芳看来,这一事件“表明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世俗对手露面了”(71页)。随着1759年《百科全书》遭到取缔,启蒙运动遭遇了危机,这彻底刺激了伏尔泰,令他决意挺身而出,为启蒙公开发声。石芳对此论道:“从这个危机时期开始,伏尔泰的小册子作品更多超脱了个人恩怨和事业竞争的范畴。”
首先是公共形象之战。伏尔泰以戏仿特洛伊之战的诗歌《青蛙与老鼠的战争》来形容这场文人论战。戏谑之外,伏尔泰倒是非常肯定这场战斗的意义,并在与达朗贝尔的通信中借用拉封丹的寓言《猴子与猫》,甘愿将“参战”的自己形容为替猴子火中取栗的猫。这样一场互相诋毁、谩骂的“争吵”,自不光彩,但无不意义,因为这是争取公众支持非常关键的一环,毕竟普通民众极易受到宣传的影响,而成见一旦形成,则难以松动。弗雷隆、帕里索、兰盖和莫罗等反哲人,将哲人们描绘成自私虚荣、哗众取宠、野心勃勃的伪君子和阴谋家。反之,哲人们则自比为遭受迫害却高尚可敬的苏格拉底,伏尔泰更是创作了一部名为《苏格拉底》的悲剧,以此为哲人和哲学辩护。卡拉斯一案成功平反后,伏尔泰成了哲人一派的标杆、社会敬仰之所向,自此不再需要借用苏格拉底的形象(173页)。不仅如此,伏尔泰继承了17世纪法国拉封丹动物讽刺寓言的传统,将一个个反哲人刻画成狐狸、狼、蛇等阴险、歹毒之形象,以作反击。伏尔泰的“笑技”,他在喜剧上的造诣,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可谓无出其右。帕里索的喜剧《哲人》和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或可与之一战。
伏尔泰的论战从未停留在粗俗的口舌之争或抽象的观念之争上,而始终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无论是与耶稣会士的笔仗,还是与或多或少受权贵支持的弗雷隆和帕里索的“对攻”,或是受其支持的德利勒和絮亚尔败选法兰西学院,都与现实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伏尔泰深知文学的政治性,他的每一次论战和休战背后都有政治考量在内,核心是争取权贵的支持和避免触犯权贵。正因此,伏尔泰对莫雷莱1760年抨击帕里索《哲人》的小册子《幻觉》颇有微词,因为后者攻击了垂危的蒙莫朗西家族罗贝克王妃。同样,由于舒瓦瑟尔公爵的警告,伏尔泰一直未敢反击帕里索的《哲人》,乃至就此事与达朗贝尔起了争执。待到说服舒瓦瑟尔公爵放弃支持弗雷隆和帕里索后,伏尔泰才开始发起攻击,着手上演剧作《苏格兰女士》。
除此之外,为了启蒙事业,身居费尔奈府邸的伏尔泰也在努力与反哲人们争夺年轻文人。许多人干谒伏尔泰,有的成功,其中成就最为斐然的当属后来入选法兰西学院的文学家拉阿普;有的失败;有的背叛,转投对立阵营,比如转投弗雷隆的帕里索。其中有不少默默无闻并将一直如此的底层文人。在罗伯特·达恩顿眼中,这些底层文人对历史的变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新作《作家的命运》(The Writer’s Lot,2025)中认为,所谓的“‘街沟卢梭’的的确确为雅各宾主义的意识形态集合体注入了激情”(28页)。
以上便是石芳笔下伏尔泰的启蒙运动。在这种语境下,启蒙已不是哲学家们的静室讨论,亦非沙龙中闲情雅致般的文学游戏,而是一场围绕着真理与权威、理性与偏见的社会斗争。伏尔泰在权力关系中进行的文人笔仗,以及将这种笔仗转化为社会事件的能力,恰恰是他的独特魅力所在。

《伏尔泰的胜利》,杜普莱西(Alexandre Duplessis)作,1775年,费尔奈-伏尔泰庄园藏。画面中央,阿波罗正要为手持《亨利亚德》的伏尔泰戴上桂冠。
社会维度的启蒙运动
对于伏尔泰而言,启蒙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立场,更是一种社会实践。从《哲学通信》到《哲学辞典》,再到一系列讽刺短文与公开信,伏尔泰反复挑衅宗教权威。他并不满足于思想层面的反抗,而是善于借助公共舆论与印刷网络形成压力,压制对手,并尽可能争取各方的支持。这就是石芳最后总结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竞争策略”(492页)。启蒙之所以是一场运动,是因为它既关乎思想的生产,更关乎思想的传播。它需要信息的组织和传播,需要盟友和受众,而不仅仅是理念。一言以蔽之,启蒙是一种社会行动,换言之,它是一种思想动员。
这样一种启蒙形态改变了文人的社会角色,石芳对此指出:“启蒙时代是文化权威的生产模式的变革与转型时代。”(486页)在旧制度法国,由于文化市场的不成熟,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宫廷或贵族赞助体系,但伏尔泰等人,他们经济独立,自主自立,通过印刷与舆论开辟出新的公共空间。他们不再只是思想的创造者,更是舆论的组织者,社会事件的“导演”。
因此,石芳新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应当承认伏尔泰的“战斗姿态”所具有的结构性意义,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层面的启蒙运动。它不同于避世的卢梭所悄然引导的激进思潮,也不同于百科全书派扎扎实实的出版事业,更不同于重农学派的行政改革。当然,这不是要忽视启蒙运动的其他方面,一味拔高伏尔泰,而是想借此指出,启蒙运动代表着一种能够激活政治活性的知识社会类型。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并不肇始于启蒙时代,宗教战争期间法国的天主教联盟和雨格诺派为了政治目的就已开展过大规模的社会论战,由此催生了反君主运动(Monarchomaques)。这样一种知识社会也未结束于启蒙运动。很快,在沉寂十多年后,1787年——此时距伏尔泰和卢梭去世已九年,为了进行财税改革,财政总监卡隆召开了第一次显贵会议,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社会论战;至大革命前夕,演化为第三等级主导的舆论攻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起码在社会运动类型上,找到了启蒙与革命的关联。思想的影响或许并不直接,其轨迹也难以追溯,但社会记忆必定有所存续。1789年之际,那些曾作为学生、佐吏、雇员和底层文人的革命者,心中怀有过去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失望,但此事看到了希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他们对启蒙运动的斗争想必记忆犹新,并利用了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竞争策略”。达恩顿之所以认为底层文人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因果关联,缘由之一就在于此。
不过,此处凸显启蒙运动的社会意义,并不是为了构建启蒙与革命的联系,这也不是石芳的本意。相反,这是在强调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运动无异。它激活的知识社会类型,已融入进现代社会中。对此,石芳论道:“经过启蒙运动的实践和认可的策略和方法,会进一步正当化、制度化,在现代社会的文化竞争中发挥基本作用。”(492页)就此而言,我们再也无需仰视启蒙运动,只消平视、思考、借鉴之。很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可能不再需要伏尔泰的现代社会,然而,这也是一个一旦需要,却再也找不到“伏尔泰”的社会。